作者:吴有水 2020-7-29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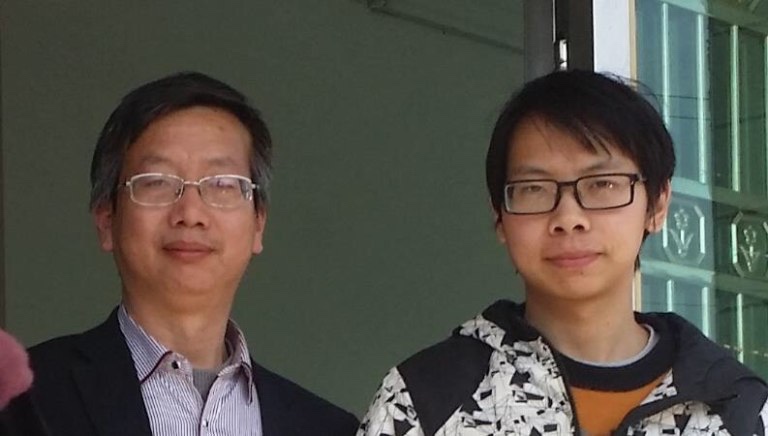
三位在看守所严密监管下,分别单独关押的“犯罪嫌疑人”,在历经237的关押后,突然,在同时提出解除自己或家属要求委托的辩护律师,而且还同时为自己委托了之前从未面谋过、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律师,为自己辩护,而且居然还同时就有这么六位长沙律师,居然分文不要,愿意接受他们的委托,为他们进行辩护。
如此的天下奇巧,我估计,只要脑袋里不全是装着豆腐渣的人,都不会相信的。
但是,
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相信,
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相信。
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那条信息之后不久,就收到了我们萧山司法局律管部门张彪的电话。他询问我,我在朋友圈发的那条信息是不是真实的,如果不能确认是真实的,最好是删除掉。
我深信,丁律师不可能跟我开这样的玩笑。虽然,从我的内心更希望,这个信息是内容是虚假的——问题是,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真实发生,正所谓,善良已经限制了你的想象。
我告诉张彪,很不幸,这是真实的。
从芜湖开庭回来后,我就开始拨打林圣新警官留给我的他的办公室电话——然而,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我又拨打办案单位其它的办公电话,结果,无一例外的是,这些所有的电话,都无人接听了!尽管,我一遍又一遍的轮流拨打着,那些电话,似乎都一直处于无人接听或者正在通话之中……
施明磊那边传来的消息也是同样。
也许,他们对我们的电话进行屏蔽了!我又试着用别人的号码进行拨打,还是无一例外的无法接通!
我之所以要打发办案单位的电话,就是还有一幻想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,三位当事人同时解除自己或者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,这不是真的。
2020年3月18日,一个来湖南长沙的电话响起。
电话中,这位女士自称是就是我儿子案的侦查单位的!
我一下兴奋起来,大声地对着手机说道:“我一直在拨打你们的电话,怎么你们单位所有的电话,一直都无法接通呢?”
她告诉我,她们单位的电话,这两天出了系统故障,所以外面的电话,都打不进去!
显然,这是一个谎话。要知道,她们单位可不是一般的单位。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通讯故障?
下面,就是这次通话的大概内容:
“这边,吴葛健雄他给你写了一封信,信里面说,他决定不让你作为他的辩护人,他会自己委托律师作为本案的辩护人。然后这样情况,我事先通知你。因为这个信件我们会以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你。相关信的邮寄内容,到时候可能会延迟几天,信件的相关内容,到时我们会让杭州市安全局的相关同志把信的内容再告诉你,可以吗?”
当即,我就问她:“你说,你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,是确实的吗?”
在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后,我又问:
“你知道我和吴葛健雄是什么关系吗?”
她说知道的,我们是父子关系,我是吴葛健雄的父亲。
我问她:是不是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委托的律师?她的回答是肯定的,三位当事人都解除了之前的律师,另行自己委托辩护律师!
不一会,我的手机又响起。
电话是施明磊打来的。她告诉我,侦查单位给她打了电话,说是有一封程渊的信将会邮寄给她。我告诉了她,信的内容应当是解除之前的律师,而且三位当事人都同样,解除了之前所委托的律师。
几天之后,收到了一份顺风快递——我去收件时,还得付邮资的。
我之前,从来没有收到过需要倒付邮资的邮件。
拆开之后,里面,正是我儿子写给我的信!
信的内容如下(全部按原文抄录,包括不合理的错字和语法错误):
父亲、母亲:
我作为您们的儿子,如今已经25岁了。但始终没有能够在父亲身边,母亲身边尽一尽孝道,更遗憾地是我跟程渊他们触犯了法律,等待我们将是法律制裁,对此我十分自责,非但没有尽孝,反而让父亲,母亲更加为我操心,担心。作为成年人的我,实在对不起您们。为了不让您们再为我操劳奔走,我决定不让父亲作为我的辩护人,而决定让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我会自己委托律师作我本案的辩护人,不再接受其他人辩护。我相信他们能够很好地帮助我,还请您们放心。
另外,我在看守所里很健康,看守所的防疫措施也很到位,也还请您两位放心。虽然目前疫情在国内好转,我还是希望您们多注意安全,少出门,也希望您们和和睦睦,不要吵架。
您们的儿子:吴葛健雄。
2020年3月14日
读到这封信的第一眼,我就知道,这封信是我儿子抄的。
日常生活中,许多语言习惯,一般是改变不了的。就如我儿子,称呼我和他的母亲,从来都只是很简单的“爸”“妈”,从来不用父亲、母亲这样正式的语言。和自己的亲人通信,一般只会用日常语言,而不会用很正式的书面语言。
更何况,信的抬头,“父亲、母亲”是顶格写的。这不符合人的行文习惯,说明,这是正文写完后,才加上去的,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顶着天花板写的情况——显然,我儿子的这封信,是事先人家写好,然后让他照着抄的。更何况:身陷囹圄的他,去哪拿钱,“自己委托律师”?
我知道了,我儿子所谓的“自己委托律师”——可能就是被迫接受了办案单位给他指定的律师,也就是所谓的“官派律师”。
我作为律师,当然明白,在中国,被羁押的刑事案件嫌疑人,要委托律师,几乎只有通过让家属来委托,即使是公派的法律援助律师,在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后,也得找当事人的家属来另签委托合同或者办理委托手续,然后凭法律援助中心出具的指派函和家属的委托书,才能得以进行会见,与当事人确认是否愿意接受指派或者委托。程渊、刘大志、我儿子吴葛健雄,首先就根本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援助的条件,不可能由法律援助中心去指派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。除法律援助律师之外,那么就能是非法律援助性质的,由家属委托的律师——否则,根本就无法进入看守所,与当事人进行会见!
程渊和我儿子在进行公益活动中,也认识有许多律师。因为他们工作的性质,需要律师来予以协助。但他们圈子里的律师,大家都是相互了解的——或者,至少是能相互认识的。如果是程渊和我儿子他们所认识的律师,那么我们几乎也全部认识或者有联系方式,他们在接受委托后,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内和我们家属联系。
但程渊的太太、我,都没有接到任何电话,说他们受到了委托,要求我们签署相关的委托手续——由此可见,所谓“自己委托律师”,很有可能就是办案单位指定的律师!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官派律师”。
“官派律师”,并不是中国律师中的某个类别。中国律师有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和社会律师三类。公职律师是指在政府中存在的,只向政府提供法律服务,或者根据政府的指定,根据法律的规定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,并领取政府薪金的律师。这类律师,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。而公司律师,是指由某一公司所设立的,专门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务部门,这类律师也不能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。而只有社会律师——或者说是商业律师,那些依靠为社会不特定的人和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,而没有专门的“官派律师”这一类。
所谓的“官派律师”,是指虽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,但官方为了完成特定案件和程序需要,专门指派社会律师去配合完成审判程序的律师。他们参与案件,并不是为了向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,而是为了根据官方的需要,配合或者帮助官方完成审判,以弥补在特定案件中法律所规定的当事人必须有律师提供“法律服务”这么一个需要。因此,律师从事这类活动,一但被发现,会被同行,或者具有一定法律常识的民众所鄙视。
所以,一般稍有良知,或者还有羞耻心的律师,是不愿意接受这种官派任务的。
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,王全璋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,听说王全璋准备委托浙江的陈有西律师为其辩护。当时,浙江省司法厅代为传达了王全璋的这一要求。陈有西律师随即去看守所会见了王全璋,听说王全璋或许有些犹豫了。于是,陈有西律师就打电话给王全璋的家属,询问是否要委托他为王全璋辩护。结果,王全璋的家属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,表示拒绝“官派律师”。
陈有西律师得知这个声明,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声明,自己并不是“官派律师”,并对事情的经过予以厘清。
陈有西律师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律师,同时也是优秀的中共党员,他的律师集团的党组织也是先进的党组织。但即便是如此显赫的背景,陈有西律师依然被一顶“官派律师”的帽子吓得半夜起来发微博发声明厘清,可见这“官派律师”的杀伤力。
那么,我儿子所谓他自己委托的律师,会不会就是“官派律师”呢?
我下定决心,一定要找到我儿子“自己委托”的辩护律师!